人最是想写东西的时候,总是听了几首曲子之后,半躺在柔软的床上,脑子步入半途的浑浑噩噩,叠加上两小时前一品脱麒麟的功效,就开始浮想联翩。
可真要落笔,又能写点什么呢?听着后朋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远视主义与俄罗斯方块的故事,最讽刺的莫过于名为“最美好的前程”的歌,就像是地铁里的那个废土,在荒芜的废土中还能找到几分文明的碎片,一时间感慨于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你真去细想,就不由得悲上心头,并非上因为某个特定事物而悲伤,而是情绪从心底漂上来,一望望不到头。可是曲子总还在放着,一首一首的接下去,或许思绪还没飘出去多远,曲子就已经到了头。
我并不喜欢后朋,不是因为曲调,是因为太过悲伤,悲伤的就像西伯利亚的一千万株白桦。就像是躺在西行的列车车厢里,裹着沉重而冰冷的毯子,看着白桦从窗口掠过,一株又一株。在你的想象中,那些白桦的背后有一个贝加尔湖,湖水清亮,在冬天会变成蔓延而通透的冰。可火车从林间划过,窗户里只是无尽的树,就像西伯利亚的冬天一样漫长的树。或许还有雪,和白桦一样白的雪。我们并非在冬天的雪中被淹没,只是冬天太长,雪又太厚,白桦也太多,看不到头。
那或许不是悲伤,是某种孤独伴随的绝望。你知道这条铁路总有前方,可火车也跌跌撞撞,或许就在什么地方撞出了轨。而雪一直在下,铁轨总是若隐若现,我们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铁路的尽头是金灿灿的克里姆林,是拥有无尽宝藏的冬宫,是依然在阳光中璀璨的阿芙乐尔。铁道的这头,是站台上卖着最便宜的肉丸子的老太太,生锈的车站标牌,走不出冬天的生活。数十年前的赫鲁晓夫楼还飘着炊烟,墙皮四分五裂,角落里渗着劣质喷漆的涂鸦。人活在历史的遗迹里,等待着一切崩塌。
或许还有希望,或许早就没有。
站在天台上望着霓虹灯的孩子,从没能走进那光里。时至今日看着霓虹的我们,也还是能感受到切身的孤独。
曲子该跳到下一首了,“团结的人民,永不被击溃”
至此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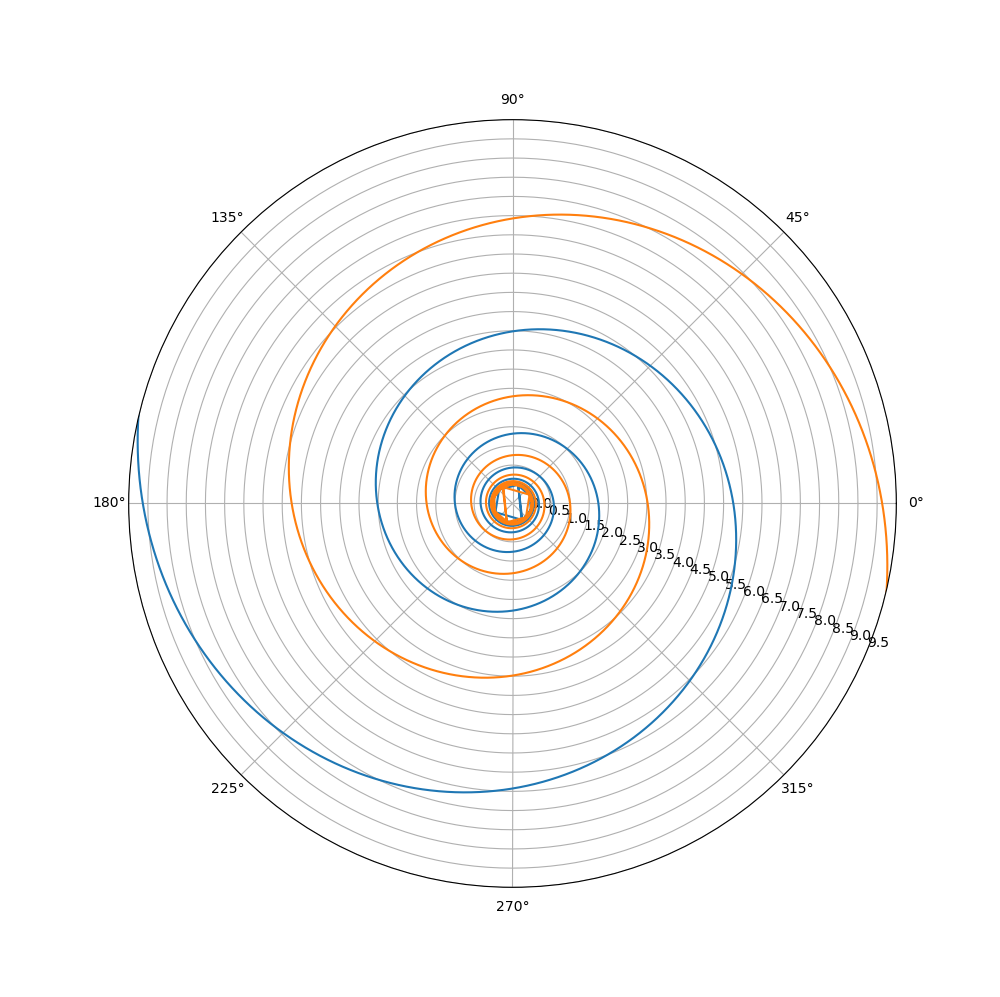
Comments |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