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之前,她依然是做了一个悠长悠长又记不真切的梦。梦里的雪好像很大,又好像不是;它们慢慢飘,飘着就飘出了梦境。
醒来后她习惯性抖一抖耳朵,抱紧被子,蹭了蹭枕头。陌生的触感。
她不怎么在意。走过许多地方以后就会发现,每一家旅店、客栈或是愿意收留她的人家,卧室里都有不同的气息;她早就对这些不大敏感,不妨说令她警惕的也并不完全在于环境。
她眯着眼伸手摸摸枕边,相机不在;才一翻身爬起来,竖起尾巴四处打量。刚来得及戴上眼镜辨认出房间的大致布局,门开了。探进头的女青年生着龙角,梳着短发,看模样比她年长一些,她不敢确定。
你醒了吗?青年望她一眼,旋即离开;不多时又折回来,手中托着的茶杯杯口热气氤氲。青年离开的十几秒钟,她寻见她的背包和相机一起躺在角落的摇椅里。
青年端来的奶茶和松饼温热着。房间里也并非没有壁炉;火焰还在跃动,可库尔札斯的冷意比她相机里的记忆还顽固。喝下第一口奶茶时青年介绍自己的名字,我叫希格,从乌尔达哈出发冒险,正游历艾欧泽亚。昨天夜里你昏倒在雪地上,我带着陆行鸟将你载回了家。
咽下第一口奶茶后,她也逐渐清醒过来,记起梦境之前她刚拍下过双子湖,正动身寻找独角兽的影迹。于是她也交代自己,莫伊拉,摄影师。赚点小钱,看看风景。
她四处为家。比起付钱住在旅店里,借住在某个人的家中显然是更划算的选择。因此她问希格自己应当什么时候离开。希格收去她手上的杯子说,跟着我冒险吧。
雪一日又是一日无止境地飞,陆行鸟也是雪色的,希格与她都穿着灰白的冬装。她们也成为两片雪花,在漫漫的土地上飘荡。
雪花见到独角兽,见到羚羊,也见到龙。龙睁开双眼时,希格的刺剑出了鞘,她的手中依然是只有相机。相机匆匆记录下龙眼的一瞥,她便隐匿在雪中残破的石壁背后。石头杂乱地堆砌,她恍惚地想,希格的家也是这样乱,衣服与背包随意地丢在一起,食物在冰箱中塞得毫无章法。
但那不是希格的家。夜晚挤在一张被子里时,希格握着她的食指对她纠正过。莫伊拉,这里不是我的家。我从乌尔达哈来,必定也不会长久地留在库尔札斯。我还有下一段旅途,还有许多素未谋面的驻扎点;像你一样。
一样吗,或许很相像。她摊开手掌让希格牵着。希格捉住的那根食指,她用来按快门;而握住她的那只左手上结着茧,那只手拿过盾,拿过刀,也拿过魔导典。她不知道希格的旅途有没有终点,她只明白她的相机该去的地方就是她的路线。
我们走吧,莫伊拉。希格握着刺剑的右手骨节分明,剑尖在风中亮出寒光,却不见血。她应了一声,跟上去之前悄悄将镜头对准了希格的剑,她想这一刻的希格如库尔札斯的雪。许久许久以来她仍旧并不完全懂希格在做什么,她也不问;只模糊地意识到希格想带自己走向远方,而她必须拿起希格的长刀。
陆行鸟腾空而起,雪原在相机里骤然降低。她一只手攥着希格的衣角,两个人的头发都被飞雪蒙上一层银白。她想问又终于没有开口,如果一起淋过雪,会不会也一起走得远一些?
忘忧骑士亭里灯光昏暗,酒客的故事和着酒咽下,也一同昏暗。她从希格带着些微酒气的嗓音里听龙族古老的传说,你知道吗,莫伊拉,人类和龙族的寿命相差甚远。人类再怎么长寿也就是区区百年,龙族却能生存千年万年。她抬起头看希格乌黑的龙角,为什么敖龙族不能拥有她十倍百倍的生命?
倘若时间会让胶片变模糊,也会让希格忘记哪一天平凡的雪,——她忽然盼望希格还有格外漫长的时间,长到足够将一场雪想念,或者足够远远地遗忘。她不能喝酒,于是想着雪,捻着茶匙,在奶茶杯中搅拌了一圈又一圈,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放凉。
我们走吧,莫伊拉。希格敞开的背包里露出书脊的一角。魔导典上有她读不懂的文字,也许同样有她读不懂的明天。她突然没头没尾地说,可是我没有剑。
她的眼神聚焦在留了茶痕的杯底,像看着她看了许多日子的雪。她成为一片长久地悬停在半空中的雪花,等待坠落,等待在荒野里融化。
她与希格也就久久地坐着。她没说对不起,也不说剑与魔导典,希格也同她一起沉默。
雪中的石屋慢慢被整理干净。库尔札斯不是希格永远的家,希格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太久,旅途也停滞了太久。她除了记得希格会去基拉巴尼亚,其实也一无所知。
她想一个人再看看库尔札斯。没有龙族,没有刀光的雪原。她想起在陆行鸟背上俯瞰的荒野,想起她问自己,一起淋过雪的话会不会走得久一些;她想,如若是看过拉诺西亚的月亮呢,看过遥远的红玉海呢,像无望的祈祷,像多么青涩的祈祷;她想,希格,你是不是也看出我隐秘地恨着你?
她转过身,拍最后一张神意之地的城墙。蓦地觉得墙上的空隙像一道锁孔,一场不可名状的雪将她困在原地。狭长的锁孔就和某天相机里的刺剑重叠在一起。
或许此时我比你要更像库尔札斯的雪。
间章一 背影
在那以后莫伊拉拍过许多次库尔札斯,每一次都复制不了西部高地的那场大雪。反倒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像希格的剑尖,决绝的刺剑尖;沉寂又哀凉,如同某种不愿意痊愈的伤。库尔札斯太大,但每一片雪花她都不陌生;那几个月里她的眼中都是黑色的龙角,那以后她看什么都是飘落的白。
莫伊拉和希格告别的那天她还举着相机,却执拗地不愿意拍下希格的背影。她模糊地知道自己脚下的这片雪地很短暂,如同对她们来说所有相遇都不会漫长。后来莫伊拉也记不得自己最后一次拍库尔札斯是为了什么,或许也没有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离开做一个注脚,仿佛按下一次快门就能安心离开。如果希格听说,或许也会想起她出发去基拉巴尼亚之前,曾与莫伊拉最后一次一起去过忘忧骑士亭。如同莫伊拉第一次在希格面前睁开眼那日,她依旧慢慢地喝着一杯奶茶;一杯奶茶见了底,雪中的石屋也渐渐冷清。一切都像首工整的诗,开头与结尾押了韵。
间章二 海色
世界还很大,莫伊拉躺在甲板上想,库尔札斯没有这么潮湿的气息。
天晴着,她侧卧在离栏杆不远的地方发呆,尾巴扫过一寸阳光,又扫回来。海上的风也有海的痕迹,她想来想去都觉得像自己,过去的日子被海水浸过,就显得太柔软,就再也难以复原。
她摸出相机来,镜头对准弥漫阳光的海面。海上反射出的阳光比雪地上要明亮,要绚烂,要更容易让她感受到自己在逃离。她仰起脸,也挪了挪镜头,一对拉拉菲尔旅人不偏不倚地闯进画面边缘。莫伊拉眯起眼看了许久许久,没看到左边披肩发的女性背着盾牌,也没看到右边短发的男性带着魔导典。她按快门的动作显得仓皇,拍完了便匆匆挪开,重新对上茫茫的海。相机里的画面失了焦,如同某天一个微醉的声音。然后她回应那个声音道,可是她没有剑。
间章三 短梦
偏偏在那个烽烟渲染的时候,希格在午后瞌睡的短梦里碰上了莫伊拉。醒来后她想起自己忘了问莫伊拉的收信地址,知道她们像半支受潮的烟,燃不着又丢不掉。她也知道远处还有战火,身旁就是战友,于是梦里她就想挣脱莫伊拉的拥抱。那个猫魅族的拥抱总是轻轻浅浅,好似盈满一种不可言说的忧伤。
可希格松开手时,只抖落了一地眼泪。莫伊拉转过身去,鞋跟碾灭了半截火星,连带着碾灭了天色。夜幕落了,梦也快到尽头,她不说再见也不道晚安,沉默又沉默,留下希格不知如何应和,最后她才从梦里掉出来,回忆比白昼短,比夜晚长。两个人分开的时候谁都没提挽留,但那天的雪色与月色又太钝,将她们的身影分开,却只切了个藕断丝连。她知道其实自己一直没松手,她们沿着时间越漂越远,她自己也被拉扯得生疼。希格拼命把这段故事往时间里埋,结果连自己也推下水去,风吹过的时候就着凉,得一场又是不知多久的感冒。
莫伊拉说服自己,她最初并不想来萨纳兰,只是在拉诺西亚坐错了一班船;不然她非要在那儿停留上一阵子,至少要把最有名的烤鱼先尝一遍。好在她沿途拍了不少照片,这才算没辜负自己在海上的那段旅途。
萨纳兰和库尔札斯太不相同。虽然她离开之前已经带上了薄些的衬衫,但真正走在萨纳兰的阳光底下,莫伊拉还是没法习惯,别扭地挽起了衣袖。这儿除了草原就是荒漠——乌尔达哈的颜色更要像一片荒漠。在旅亭里开间房住下,整个房间也如同沉默的风沙。
她趴在旅亭的床上翻地图,琢磨自己该去哪儿赚钱,再去哪儿取景。莫伊拉支撑起身体,往一旁的镜子里瞧了瞧自己。不像矿工,也不像商人,要是当个纺织女工倒还算合适;但和希格待在一起的几个月,她已经习惯了住在那间石屋里,做做饭、整理房间,随着希格出门时躲在她背后,手中只带着相机。莫伊拉不自觉用右手摩挲两下地图,犹豫了一瞬要不要去买副趁手的工具。
她起身简单收拾了背包,下楼往最近的市场去。
阳光下的街市也陌生。她想,伊修加德可没见过这么热闹的街道。
路旁摆摊吆喝的商贩,玩杂耍的拉拉菲尔族人,还有她在人群里突然对上的一双眼睛。莫伊拉停下来,掉进那双清湛湛的蓝色里去。
那个人在跳舞。莫伊拉的目光穿过密集的观众。人们偶尔落下几句散碎的私语,说这是从贫民区临时被招来的舞娘,平日里在这里工作的猫魅族似乎身体抱恙……她望着那个人的模样,陌生的金色的长直发,还有她太熟悉的乌黑龙角。敖龙族的腰身比背后两个猫魅舞者更窈窕,四肢要更纤细;莫伊拉不清楚是不是由于难以启齿的生活环境。
她没有在库尔札斯见过几名舞者。雪国的人们将自己用棉衣裹藏起来,身材在大雪之中并不那么重要。至于乌尔达哈——对,乌尔达哈。莫伊拉该死地记起了另一个拥有深蓝色眼瞳的人,她旅途的起点就偏偏在这座城邦。
希格,你说萨纳兰的阳光这么好,为什么你一定要走向雪国?
似是注意到莫伊拉的视线,金色长发的舞女朝她这边抛了个飞眼。她垂下头去。这个人没有希格的眼神;她要更温柔、更热烈,更像萨纳兰的天气。莫伊拉转身走远,音乐也变淡,如同陆行鸟腾空时整片大陆的影子都模糊。
“小姐,别急着走,别急着走呀。”台阶边上戴着头巾的拉拉菲尔人一眼看出莫伊拉的装扮不像本地人,极力劝她买点他酿的酒喝。“您看酒馆也不远,来乌尔达哈一趟,不喝点本地的蒸馏酒是真可惜呀。”
乌尔达哈就是这点最麻烦,她心说。她本想礼貌回绝自己并不能喝酒,心中却轻微地动了动。她听见自己应允一声,于是继续逛街时她鬼使神差地端了一杯。——但第一次碰酒的她显然做了个不那么明智的选择,一份酒一会儿便下肚,不多时她就已有些发昏,又微微红了脸颊;还好她已经坐在流沙屋里。
等到莫伊拉确认自己稍微好受些,再折回红玉大路时正是黄昏,舞娘跳着最后一支曲,新来的舞者依然站在中央。她依然不久便注意到莫伊拉,依然抛来一个含笑的眼神。
还是不该喝酒。莫伊拉用鞋跟磨蹭着地砖。她一看向那个舞女,就见到一双萨纳兰的天空。
萨纳兰,萨纳兰。她想,那片天或许就来自几个月前,或是几年前的萨纳兰。
观众吵嚷起来,多半是叫好,夹杂着几句下流的起哄。于是莫伊拉回过神,意识到舞曲结束了。他们早从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听说新来的舞娘出身于白玉小巷,嘴碎的穷人们猜她会不会已经出卖了初夜,富商们吹嘘扬言要千金买她的身体。敖龙族的女子不理会,大方地行了一礼,拢好垂下来的发丝,向雇佣她的商人结了工钱就离开。
她收了钱,离去的方向恰是莫伊拉所在的方向。只是莫伊拉没料到,她在自己身边顿了一步。
“你在看我。”她悄声笑道,目光狡黠。
看了又如何?莫伊拉抖抖耳朵尖,“看你的人多得是。”
“你住哪儿呀,要一起吗?”她回过身,一下勾上莫伊拉的肩膀,“去喝一杯?还是说你刚喝过?”
“沙钟旅亭。——但是刚喝过。”莫伊拉算是默许她同行,只是脸颊又温热起来。她知道自己不大能喝酒,也猜到她们大概是不顺路的;可这个人的眼睛让她受不了,也让她说不清。似是躺在拉诺西亚的航船甲板上看荡悠悠的晴空,没有云。视野里是连绵的没有尽头的蓝,那时她总是恍惚间错以为这是一片蓝色的眼盲。
舞女轻轻笑了一声,鸟鸣一样短促又嫣然的笑。“走啊,就在隔壁。”她靠过半个身子,扶上莫伊拉的手臂,“我叫卡洛塔。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冒险家?”
“莫伊拉。——我不是冒险家。只是个摄影师,流浪的那种。”
“你的名字可不像个猫魅族,莫伊拉。”
“你更不像敖龙族……。”
说话间她带着卡洛塔推开了流沙屋的门,卡洛塔也没再提要她喝酒的事,只是一路随着她向她开的房间走过去。“那又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家,我也根本不必按照东方的方式取名。”卡洛塔边爬着台阶边懒散答道,“照你的话说,我们都不是冒险家。可是我们和冒险家有什么区别?我们都谋生,都挣扎;人们传说的那位光之战士,那不叫冒险家,那叫英雄。把她称作冒险者,我们又是什么?这反倒太侮辱冒险家。”
等到莫伊拉关上旅亭房间的门,卡洛塔的气息从她的左耳边吹过来。“我猜你还没完全酒醒,小冒险家。”
莫伊拉勉强退开一步,“你是想要什么?”
卡洛塔不恼,自然地松开她,顺便理了理身上轻薄的纱裙。“没什么,只是我猜你想要我。我说了我发现你在看我,你的眼神不一样。”见她不语,卡洛塔的眉眼又弯起来,“这当然猜得出来。我是白玉小巷里卖艺的,总该有那么些本事。没点察言观色的伎俩,要我怎么挣口饭吃?”
卡洛塔走上前,重新坐在莫伊拉身边,让她搂着自己,又握住她递过来的食指。莫伊拉左手的指腹蹭得卡洛塔腰际发痒。她正禁不住要躲闪,却被莫伊拉一股力气扳倒,大半个身子被拖上略显拥挤的双人床。
“我有点累,希格。陪我休息一会好吗?”莫伊拉的最后几个字像被磨碎了,从口中轻飘飘地吐出来。她埋进枕头,从衣服里摸了两枚银币递给卡洛塔;卡洛塔望着她,抿了抿唇。最终也只是顺从地躺在她身边,重新攥上她左手的食指。
卡洛塔的长发散在白净的被单上。
莫伊拉眯起眼不想睡,侧卧着发呆;她没意识到刚刚自己在困倦中叫错了名字。卡洛塔的金发像她在航船上拍到的海面,波光闪烁着勾成了线,连成一片,一直漫到记忆里,也烧痛了她的双眼。卡洛塔,卡洛塔。她不像希格,莫伊拉想,卡洛塔的名字读起来有点儿拗口,听起来反而轻巧,灵动。俨如舞步。她的长发和她的舞蹈是一样的味道,灿烂的古典玫瑰的气息、萨纳兰的沙和艳阳的气息。
那个人的名字她独自念过许多次,柔软的、缠绵的、两个暧昧的音节。她从出现到离开一直留着短发,一直是雪的味道。莫伊拉也不好说究竟是希格来到库尔札斯太久,还是库尔札斯的雪太大;那个人与那个人的剑都变得冰冷,在莫伊拉的眼前落下,又在她路过的地方融化。她模糊地梦见自己曾经行走的雪国,梦见深不见底的云海,还有同样深邃的龙的双眸。
卡洛塔捉着她的左手,拾起来,挑逗似的吻了吻她的手背。
莫伊拉被惊醒,怔怔地注视着卡洛塔。她仍然穿着那身纱裙,衣料滑下肩头,露出更大片的肌肤。“醒了吗,小冒险家?”她笑,“以后喝多了酒的时候,别把别人的衣服当被子往自己身上扯,知道吗?”
“我睡得久吗?”“不久,亲爱的。”她扶着莫伊拉坐起身,“十分多钟。现在你打算做点儿什么?”
莫伊拉不答。她侧过身将额头抵在卡洛塔裸露的右肩上,感到身体里有一汪泉水正在干涸。卡洛塔的裙子不长,她合上眼,一伸手就触碰到纱裙下修长的腿。她的手指用了劲,像要攥住一支黄玫瑰的春天;白皙的皮肤被抓出指痕,泛着红,卡洛塔没出声制止,直至莫伊拉放弃般地一点点松了力气。
我们走吧,卡洛塔。
“什么事情这么急?”卡洛塔才终于将上衣理好,挑眉道,“我收了你的钱,至少总要跳支舞给你,或者别的什么。”
“我不想——我要回一趟库尔札斯……”莫伊拉解释不明白自己的想法。只是她忽然感到卡洛塔跳舞的模样太陌生,只是刚来到沙之都,又唐突地想念起雪国的石屋。
“我就说你是个小冒险家。你住那儿?”
莫伊拉又摇头,她只是与希格共同在那儿存在过。她没有家。
“你才刚来没多久,莫伊拉。”卡洛塔的言语犀利,缓缓贯穿她。“即使你回去了,你想的人也不会在。”
等到莫伊拉离开萨纳兰的时候,她已经能够从容地喝下一整杯蒸馏酒了。那个卖给她第一杯的拉拉菲尔告诉过她,乌尔达哈的蒸馏酒和别处的味道都不一样;但卡洛塔问起时,莫伊拉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这还是她尝过的第一种酒。
卡洛塔替了那个猫魅族舞者四天的班,此后就没太去过红玉大路,反倒是经常来找莫伊拉喝酒。但莫伊拉三天两头地不在,隔几天才回一趟乌尔达哈。能遇见时,她就把自己的相机丢给卡洛塔玩,絮絮地讲述北方的水晶被称为卫月的爪痕,南方的沙漠是传说中神火燃烧的地方,说萨纳兰的弃石像库尔札斯的云雾街。云雾街——讲到这儿,下一句话就卡在了喉咙里。因为她看着面前垂下眼睛喝酒的女人,那个影子慢慢就和库尔札斯的自己重合。
撒沟厉沙漠也如同航船底下一片破碎的海,也如同漫无边际的雪原。莫伊拉换回棉衣,伸出手去接久违的雪花。她到底是回了石屋,门前的邮箱上薄薄地停着一层雪。邮箱的小门许是生锈了,刺耳地喀吱一声;里边躺着数个雪色的信封,莫伊拉忽然错觉邮箱里的雪比外边下得更大更冷。
她站在雪原里一封一封地拆信,最上面的信封角落里有一处似乎曾经险些被烧焦。莫伊拉,你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你是不是还住在这儿。多玛的事情快要终结了,我想阿拉米格也不远。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你可以把这里当作你的家。
抱歉,莫伊拉。我的信写得越来越短了。战事太紧,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你从库尔札斯离开了吗?我想如果到了战后,我可以带你来基拉巴尼亚,带你来一趟草原,来看看延夏。可惜的是你不太会潜水,我多想让你也见一见红玉海的海底。如果我能够回来,该去哪儿找你?
你见过草原吗,真正的草原?听说这里才是我真正的故乡,这里有许多与我相像的敖龙族。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儿,但我只感觉到陌生。莫伊拉,这里有我的许多同胞,却并没有我的伙伴;我的记忆开始在沙漠,那里是我的起点与我的家。你呢?如果真的有可能,我也想到你的过去里旅行。
莫伊拉,我越发觉得你应该来东方看看。我很想带你逛一逛黄金港,你爱吃甜,或许这里的团子会合你的口味。只是现在的多玛还不属于多玛人,如果这里终将解放,我想黄金港会繁华许多。那时我们再一起来吧,带上你的相机;这次我还是来做你的导游,但那时我应该就不必再时刻带着刀了。如果你想要回信,寄到乌尔达哈商会馆就好,会有人替我签收。
最近好吗,莫伊拉?你一直没有固定的地址,我只好把信寄到这里。希望你还住在这儿,至少有时会回来看看。我最近在基拉巴尼亚活动,阿拉米格的事情还等着我来解决;但是不必给我回信。这边比你想象的要更乱,寄信是件有点儿奢侈的事情,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每一封信都能送到这座屋子旁的信箱里。如果可以,我们再在这里见吧,我带你来这边拍更多的照片。
库尔札斯的阳光并不温暖,但照在雪上时却没来由地刺得莫伊拉流泪。她无端地想起了萨纳兰,那儿有无边无际的艳阳天;想到一支金色的玫瑰浸在酒杯里,和阳光的颜色无异。心事都泡成了醉意,就慢慢沉默,下成一场无名的雪。
间章一 盛放
莫伊拉不知道雪天里的花能活多久。在她还没回到石屋之前,卡洛塔给她的玫瑰就渐渐凋败。她想,似乎她总是有一个最后一次,不回头,只怀念。最后一次被卡洛塔拉着喝酒时,卡洛塔没说再会,只是在她端起杯子时递给她一支黄玫瑰。黄玫瑰在昏暗的灯光底下开得黯淡,多么配萨纳兰的沙海。她将玫瑰放在酒杯后看了又看,终于也没有拍照片。
她心里清楚,以后她大概不会再见到卡洛塔。但再想起卡洛塔的名字,她仿佛总能陷进雪,而不是沙。石屋里的第一眼还是雪夜的背影,她不好说,也许都没来得及放下。她发现那个背影才最像那一支灿烂的明黄;她的心里大雪乱飘的几个月里,希格在雪地的边缘自顾自扎了根,开得好烫好烫。
间章二 火枪
斯特凡尼维安将火枪交给莫伊拉时,她有一霎时的心虚和迟疑。希格离开了伊修加德,龙与战争的故事一并变成了过去,机工士似乎也成为上一段时代的遗留。莫伊拉背起枪在灰色的城邦里淋着雪,慢慢走,淋上一肩的心事;枪口仿佛还沾着相机里的剑光。她的头发半长不短,披散下来嫌长,扎成马尾嫌短;心绪也散乱,抬头是铁青的天色,低头是指腹摸索的扳机。
英雄归来后该去往何方呢?她走着就到了云雾街。石屋里的等待会像雪原一般没有尽头;云雾街不长,故事倒是在酒馆里讲不完,她想还是这里与英雄最相配。那支黄玫瑰掉在莫伊拉心底,就是一声枪响空虚在黑暗里。一瞬间的走火里,黄玫瑰也开了一个刹那,短促得只容许她想起希格的名字,另一句想念却始终说不出;莫伊拉持枪的身形也渐渐锋利,生生将这半句逼回了喉咙里。
间章三 雪夜
酒馆里男人的声音张扬到九点半,莫伊拉捧着一杯蛋奶酒听到九点半。男人放下钱袋时莫伊拉放下杯子,心照不宣般就出了门走上同一条路线。后来云雾街的角落里不知是第几次有人付给她钱,她声音哑着本想说谢谢,终于还是沉默着回过身走开。头一回接这种活的时候,是她几乎要吃不起饭,咬牙犹豫了差不多一星期才答应下来;她以为自己在怕,可那以后她才知道自己端枪的手可以与拿相机时一样稳。
背着枪时莫伊拉习惯一个人走,也不说怕被人寻仇。到了宝杖大街前她停下来,倚着栏杆又开了瓶酒,此刻她像是才想起来发抖,不经意间洒了几滴掉进夜色。印象里雪原里的夜比城中更暗,所以她与希格的指尖碰在一起时,就讲不清是有心还是无意。没拿着酒瓶的那只手碰到栏杆,她不自觉地抓住,面向恒久的冬天,背向掉色的回忆;她的脊背用力顶着枪管,心想的却是如今的她该怎么制造一场陌生的重逢。
城里城外尽是灰白色的冬意,伊修加德向来是这样的地方。
希格将金发留长了,她学着莉瑟的样子将马尾束在脑后;披肩的头发对于战斗总是一种累赘。她从第一世界回来,有太久没回到过库尔札斯,已经不大习惯这里的气候;仿佛那年在雪原里漫无目的地行走的几个月,都随着莫伊拉的胶卷丢在角落里。雪飘飘洒洒地渐渐下大,她向衣领里缩了缩头,解下高高绑着的发绳。希格忘了戴围巾,长发盖在颈侧,她想或许至少也能挡挡风。
于是雪在她的金发上慢慢停下来。行走在街道上时,她也就如雪地里一棵半枯的树。
灰白,灰白。伊修加德在风雪里长久地沉默,拥有着长久的冬天。
希格是第一次来到天穹街。她从云雾街一路穿过来,气球的颜色就撞进她的视野里;和云雾街的昏暗搅浑在一起,灿烂得生疼。
庆典的喧闹与柜台前的嘈杂令希格一时间不知所措。听着当地人将民众的生活讲得天花乱坠时,她还背着自己在龙堡时常用的那把刺剑,站在一群同纺车与锤头为伴的工匠中间,总觉无所适从;同是喧闹,她此时更想退回忘忧骑士亭,宁愿听喝醉的人耍一耍酒疯。
因此她逃了。在暂时摆脱热情的引路人后,她几乎本能地回到云雾街去,绕向曾经多次与居民寒暄的酒馆。
酒气,吵嚷,碰杯。她分明是推门走下台阶,走向另一处写满了故事的所在,却像是躲进僻静的角落里去。一份鸡尾酒——她顿住,在招牌上搜寻曾经熟悉的名字,冻——雾,鸡尾酒。店员爽快应下,收了钱转身去干活;希格一只手肘撑着柜台,合了眼听周围的声响。
近来这里似乎也并不太平,说是有个新枪手冒了头,动不动带着狐朋狗友闹出什么乱子……她轻叹,说不准这个委托不多时就要找到自己头上,她干多了这样的小事。酒上了桌,她倒一满杯,往喉咙里吞。离开库尔札斯后她很少再喝酒,可这般的大雪永远让她有一醉方休的冲动。
远远地响起杯子碎裂的声响。希格斜着眼向声源处一瞥,望得见陈旧的楼梯,看不到楼下的人。她将杯中剩的半口喝干净,端着瓶子下楼再探头。店员不在,只有几个酒客围着靠门的桌子笑闹;三五个人簇拥着的女子穿着和天气并不相称的衣服,张扬地坐在吧台上,身边赫然是一把同样张扬的枪。
希格注意到楼梯下躺着一地玻璃碎片,想是他们中的谁刚刚丢过来,或是用子弹打碎。她绕开,走到吧台另一端重新坐下来。
她又倒了满杯的酒,端起来却迟迟咽不下。
希格没敢再看一眼那个拿枪的客人,可酒精苦涩,她的记忆也发涩。陌生的短披肩,陌生的长裤,连桌上的火枪都同样陌生;但她最后望见的是女人暗红色的双眼,希格哽在喉口的酒告诉自己,她该认得那对眼睛。不应当。她想。那么柔软的眼睛本是躲在相机的镜头后面,可从来都不是瞄准镜。
通向云雾街的门开了又关上,雪花从酒馆入口闯进来,木门呻吟的动静在风声里都显得欲言又止。
来吧,英雄,聊聊天吧。店员仍是不在,客人已心照不宣地离开,莫伊拉扶着桌沿翻身下来,踉跄到希格身边的位置落座,一张口就是醉意。
希格恍然才明白。她以为自己在逃,可她忘了自己怕什么,她似乎无论去哪里也不该回伊修加德。伊修加德拥有长久的冬天,冬天贯穿了她同那名摄影师走过的所有日子;雪花钻进她的衣领,她的记忆就在灵魂里打颤。
“莫伊拉。” 她想问怎么今天没有点奶茶,话到嘴边又差点变成你的相机带了吗。
“你知道吗,英雄,现在在云雾街,他们都叫我火花。”希格刚艰难地开了头,莫伊拉便眯眼笑起来,伸出食指封住希格的唇。“现在我是火花,枪口里迸出来的火花,云雾街的麻烦,他们嘴里爱闹事的枪手。”
英雄,你看,我也拿得住枪啦。只是可惜它没见过多玛。莫伊拉伏在桌上,留长的头发一绺一绺落下去。在多玛之后呢?你去哪儿了?这些都不重要。你要知道,那时候你想教我练刀,可现在我也拿得住枪了。
我惹上麻烦了,英雄,但我成了云雾街的火花。可别像我一样,总在云雾街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还是接着做英雄适合你。逮捕我或者带走我吧,希格,我和你说过没有,你拿剑的样子像什么?像库尔札斯的雪。
希格含着口酒,听她细碎的话语掉出来,没回答她其实雪其实从第七灵灾以后才漫无尽头地下,只是许多人都忘了而已;库尔札斯的气候向来都没有永恒,她拿剑的样子和莫伊拉拿相机的样子都是。
缓了口气后希格道,“你的头发也长了。”
我喜欢,亲爱的。莫伊拉咬字朦胧,清晰的只有叹息。
小小一壶让希格喝得很慢,瓶子空了以后她低头看,莫伊拉的枪丢在一边,人已经睡熟。她将枪放进怀里揣好,扶着莫伊拉起身去楼上开了间房。希格并不喜欢九霄云舍的装潢,不曾改变的灰白像囚笼,将她们一起困在伊修加德走不出的冬天。
莫伊拉睡着时,希格又去了一趟天穹街。她收起刀,披着大衣行走在广场里;有人聊起半个月前袭击了庆典又销声匿迹的火花,有擦肩而过的路人对伙伴低语,听说英雄也来了天穹街。
英雄。希格回到旅馆里,推开房门的前一刻突然想起那句话,想起莫伊拉也这么称呼她。她记不住自己什么时候从冒险者成了英雄,做的事却不声不响地一点点变大,从乌尔达哈的一个窗口出发,恍然间才发现一把剑就挑起了半个世界。门的响动惊醒了莫伊拉,希格见她依然是抖抖耳朵,抱紧被子,无意识地蹭着床单。只是她没有去摸相机,也没有一不小心摸到希格的角。
“下回少喝点,把自己用来犯事的东西看好了。”希格解开衣扣将枪还给她,金发上的雪还没化。
莫伊拉目光在希格身上停滞半晌,旋即浅笑,“你又去忙了。这次你要在库尔札斯停留多久?”她捋着发梢,问得漫不经心,仿佛希格离开对她而言稀松平常。
希格将外套丢在一旁的桌上,坐到莫伊拉身边,看到她已习惯性握住了枪。“莫伊拉,在第七灵灾之前库尔札斯曾经是山区,这里没有长年累月的雪。”希格忽然将吧台上咽下的话说出口,头顶的雪色逐渐不见踪迹。
所以我早讲过,我比你更像库尔札斯的雪。莫伊拉话出了口才意识到她其实没说起过。第一次这么想时,希格或许已经动身去了东方,而她握着相机,在神意之地拍某一段城墙。
希格再望那对熟悉的眼睛,像浑浊的日落。莫伊拉是雪,也是雪里最冷的火花。她从某一刻开始坠落,自此就游荡着留在冬天。随着风漂泊到希格的旅途里时恰好是一场大雪,漫天的白像一场烧遍了大地的火灾,叫希格一次次地迷了路。
算啦,希格。她开玩笑地说,别带走我了,逮捕我吧。
分明是莫伊拉被困住,她也情愿再被希格困住一次;希格却感到从自己逃进酒馆的角落里开始,这对眼睛就下起雨。她没带伞,在狭窄的屋檐下哑口无言。
如同某种妥协般地,希格闭起眼躺倒下来,攥住莫伊拉的食指。
睡吧,不早了。也许再过一阵子才离开,剩下的慢慢说。
莫伊拉住在希格花钱租的旅店房间里。希格白天去天穹街,她有时跟着,有时感到百无聊赖便出城。回了房间碰见希格,她将枪重重丢到床上,看见没有,我也拿得住枪了。
希格失笑,我去过的地方,拿得住枪也不一定活得过多久。她又说,再过几天吧,可能我该再向东方走一走。
“你头发长了,英雄。”莫伊拉回过身,捡起枪,又捡起扔在角落的背包。
“少犯事,莫伊拉。”希格答非所问,“希望我下回找到你的时候,不用摊上逮捕你的麻烦。”
莫伊拉用枪托砸在地上的闷响回应她。
希格从手腕上取下发绳,默不作声地重新将头发束高。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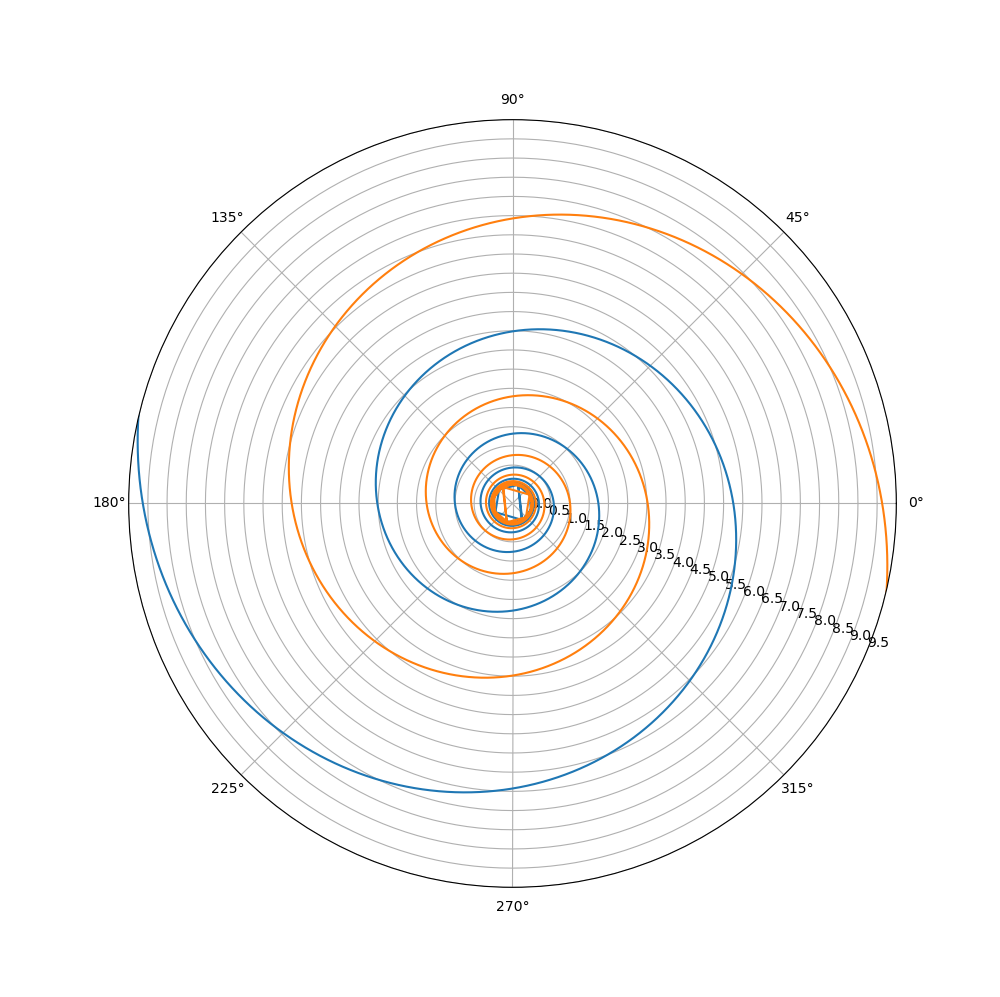
Comments |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