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天垓没有邮差。
总算是下定决心从库尔札斯离开后,希格向东远行。黄金港铁匠锻造的打刀她拿来试了试,用不惯;三彩团子她吃起来嫌有些甜,但她记得刚与她分别没多久的猫魅族也许会喜欢,毕竟莫伊拉嗜甜,皱着眉说什么也不要喝她的鸡尾酒,硬要在酒馆里点杯格格不入的奶茶。
莫伊拉,
我越发觉得你应该来东方看看。我很想带你逛一逛黄金港,你爱吃甜,或许这里的团子会合你的口味。
只是现在的多玛还不属于多玛人,如果这里终将解放,我想黄金港会繁华许多。那时我们再一起来吧,带上你的相机;这次我还是来做你的导游,但那时我应该就不必再时刻带着刀了。如果你想要回信,寄到乌尔达哈商会馆就好,会有人替我签收。
希格没写落款,后来也没收到回音。
那些日子战火烧得越来越盛,她寄到库尔札斯的信笺越来越短,身形在自由或是死亡的高呼里被压缩成信笺般的单薄;不变的是信的开头仍旧一句句重复着,莫伊拉、莫伊拉。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挂念。
猝不及防前去的第一世界没有月色,她静不下心,索性就不再写有去无回的讯息;一直到她逃回伊修加德的雪色,那天晚上她听见莫伊拉的子弹将玻璃杯撞碎。没多久她重新束高了长发,航行向知识的城邦。那以后她习惯坐在海岸边借着晚霞写信,日落后就放下信纸仰头望着星空直到困倦,送出的信总是没有落款只有开头;但莫伊拉很少回信给她,寄来的纸张上字迹敛着、情绪也敛着,有时附上几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从伊修加德向外眺望的雪夜。
莫伊拉,
我相信你还会回到这座石屋,早晚会回来;但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写信。最近这边的情况不太好,我很担心你。可以的话,请把信件寄到萨雷安的巴尔德西昂分馆。
如果一切都可能结束,我想带你来看一看北方的伊尔萨巴德大陆。这里是你再熟悉不过的海岸,然而这里有拉诺西亚见不到的斑斓。希望那时你还和从前一样喜欢喝奶茶,不知道近东地域的调味你能不能喝得惯。
最后站在宇宙极致深邃的地方时希格手上依然是一把刺剑,剑刃上隐约的光从摇曳的花海一路亮到死灭的太阳。事实上后来希格几乎没太换过武器,同一把刺剑被她一遍又一遍擦得几乎发白;自从——自从那天在酒馆里有一个弥漫酒气的声音对她说,你拿剑的样子像库尔札斯的雪。
握住剑柄时的希格总是知道自己是谁;被使命定义的光之战士,擎起刺剑与触媒、除了战斗一无所有的英雄。从最初燃烧天空的赤红尖角,到终焉晖光粼粼的金色涛浪,她背上了太多或来自人间或远在星海的目光,刺剑将她蓝色的瞳仁引燃——除此之外她不愿多想,希格愈发地以一种近乎灼烧的眼神对上敌手的视线。
只是离开天际时她蓦地感到自己被抽空,错觉自己也成为被星壳围绕的一片空洞宇宙。天外天垓没有邮差,她想。
希格松开右手,刺剑坠落在不见边际的虚空里。
钻进旅馆房间以后希格反锁了门扯下披肩,和外袍一起一股脑地压进箱底;挑挑拣拣翻出一身短外套,束起的马尾剪短,把自己的过往也剪短。碎发和她作为英雄的履历七零八落掉了满地,剩下的不及肩。希格简单整理两下,镜子里不过一个穿着干练的灰扑扑的敖龙族,身上的一切拼出一个暮晖之民的路人;或是别的什么也好,只要不是宇宙尽头的冒险者。
只要不是那个宇宙尽头的冒险者——
在她还没有被称为英雄之前,大家都习惯于叫她冒险者,甚至一开始是那个“醉以太的冒险者”;那时人们见到的希格永远系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一路奔跑。她从乌尔达哈的一个窗口转过身,一路跑进暮色四合的海港,跑进草木生长的城邦;然后她伏在陆行鸟的脊背上前行,从沙海、森林到丘陵。
再然后到银装素裹的库尔札斯。
可她跑得太快,被一场大雪绊倒,摔进一次简短的邂逅。雪原里的莫伊拉手无寸铁,面对希格时却有一个哀哀的眼神出了鞘。希格拦不住,莫伊拉刺破了陆行鸟的鸣叫,又划花了行星的低语,留给希格一场漫长又无处医治的耳鸣。
如果是莫伊拉,希格在回到格里达尼亚的飞空艇上想,如果是那个雪原里的莫伊拉经过了黑衣森林,她不会像风一样路过树梢;她要下成一场细密连绵的雨,要带着她的相机和札记,步步打湿每一棵树干的每一寸沟壑;可那是希格构想的莫伊拉,但愿也是如今的她。和希格自己写的信一样,没有依据没有承诺,一切都只取决于如果。
希格在栖木旅馆里写自己的下一封信。
莫伊拉,
从天外返航以后我去忘忧骑士亭找过你,店员告诉我你要过一阵子再回来,还请了我一杯鸡尾酒,说是你留下的钱。我想大概你也不在库尔札斯;你的家在拉诺西亚,先前去过一趟萨纳兰,于是我跑到黑衣森林来碰碰运气。
我将刺剑丢在了宇宙里,可是这时悚然发现除了剑我几乎一无所有。回到亚伊太利斯后我感到自己的精力以光速流淌,时间却被一帧帧放大;没有人为了哪一个国度、星球或是世界来寻找我。
希格的笔尖顿住,迟疑了能有一阵风经过她窗前的时间,终于迟钝的想念还是说不出口。
如果你收得到、如果你愿意,那么我在格里达尼亚的栖木旅馆。
她将信笺折好装进封筒,推开椅子下楼去寻找邮差。收件人的地址仍在库尔札斯西部高地,然而在信封角落写完这行字,她忽觉手中的笔如小刀,切割一支蜡烛般将自己的一部分缓缓剥离,一起埋进雪地里。邮差莫古力用不变的库啵声作为回答,将她的心事一视同仁地揣进邮差包。
“谢谢。”希格压低声音。知道不会有回应,也许本就不是讲给莫古力听。
希格想,怨她太早遇见了莫伊拉。莫伊拉喜欢用看风雪的神色看她,只有风雪,没有愿望,没有譬如替谁守护一个雪不停歇的城邦。她的眼睛潮湿,含着冰河一样冷的此恨悠悠,望得深了就酿成一场席卷的雪崩,盖住情绪,覆过情欲,扑面而至,连根拔起希格对自己脆弱的期许。
希格喜欢在烤饼干时走神。
住进栖木旅馆以后日子大段大段地空白,希格放下了剑也放下了姓名,失去了战意也不再有委托,身上的时间被抽去筋骨,散落成一片破碎的海;于是出门闲逛,想着哪怕这是用来补偿自己匆匆掠过的最初的冒险。
黑衣森林的树木在枝头纠缠,织成漫长的迷宫,遮掩住大半的天空。她走在草地上仰头看,像海倒悬。
林间几乎不下雪。但落叶偶然向她飘下时,她发觉自己如同走过了一个肃杀的冬天。希格一肩背着包,手伸进口袋,碰到莫伊拉为她寄来的照片的一角。它曾经戳痛过她的指腹,现在几乎被磨出毛边;粗糙的触感缓缓摩擦,像生锈的小刀钝钝地擦过手指,她才发觉自己一个人时,陷进回忆的时间越来越长。
所以在她看到商店街招募板上的广告当晚,就乘渡船前去薰衣草苗圃。正在招收人手的咖啡馆门庭冷落,不大的店面中只有两个精灵族。柜台里的女孩悠闲地磨咖啡,她不远处的沙发上青年低垂着头练吉他,女孩略一抬眼,欢迎光临。喝点什么吗?
希格要了杯滤挂咖啡,女孩转身去煮开水;青年没理会,抱着琴自顾自地弹。等到端上桌来的咖啡稍微变凉,希格尝一口又加了半勺糖,才解释自己是来应聘。会做些甜品,如果你不介意。
女孩点一点头,将吧台让给希格,和沙发上的青年耳语几句。青年比希格身材高大些许,来到她身边拉开抽屉,将玻璃罐一个个摆上桌,俯下身低声地交代罐子里的每种原材料,让她随意用。
背包里也带了些食材。希格烤了半盘松饼,两块蛋糕,塞上几枚饼干把托盘填满;店里渐渐地来了三五个客人,两个精灵族的店员有时从她背后钻进柜台忙碌一会儿。等她将盘子端给青年时最后一名顾客的茶水正喝了两口,他示意希格稍等片刻,和女孩坐在靠近吧台的一桌。客人离开后女孩向她回过身,谢谢你愿意来帮忙,欢迎你。我叫卡米尔,我哥哥叫提米奥。我们怎么称呼你?
我叫——希格意识到忘了给自己取假名,插进衣兜里的手不自觉摸索着照片边缘。
可以叫我火花。
卡米尔和提米奥对视,应该是没见过这样取名的敖龙族;最终也没计较,向她伸出右手,又道了一遍欢迎。
此后卡米尔煮咖啡泡茶,提米奥和希格烤甜点。希格等着饼干烤出香气前喜欢靠着柜台发呆,没人时就听卡米尔在远离柜台的角落独自拉琴,或是提米奥慢慢弹着吉他,有人时目光就扫过零落几个客人,没有一个是暗红色眼瞳的猫魅族;再翻翻留言册,也没有谁的字会写得一笔一划,简短又刻意地冷硬,墨水晕开在字母的开头。
倒是隔了一阵儿有个乌发碧眼的猫魅族来应聘,自我介绍说叫伊芙,留在了店里就每天哼着小曲快活地跑前跑后。有常客夸她的嗓子动听,她便扭头望着人家咧开嘴笑出声来,露两颗尖尖的虎牙,又因为没看路一头撞在希格面前的柜台上。第二天还照常来上班,却是自作主张带了话筒来,兴奋道我们几个人一块唱歌吧,万一有人喜欢,来的客人还能再多些呢。卡米尔和提米奥还是对视一眼又默许地低头顾着各自的琴弦,留下希格在练琴的兄妹两人中间张口结舌半天,勉强说自己半吊子地学过键盘,也算能认识乐谱。事情就这样叫伊芙潦草敲定下来,比希格的信还要没谱。
伊芙一蹦一跳地跑到院子里去晒太阳。希格想她无厘头的性子倒并不讨人厌,只是比起卡米尔和提米奥更像想当店长的模样。
咖啡馆太小,没有地方搭舞台。伊芙张罗着挪开桌椅凑出一片空地,招呼希格把她的琴搬来,自己在一旁架起话筒;环顾四周却没有找到电源,想到卡米尔兄妹俩本就寡言少语,咖啡馆更是不宜太过聒噪,就只好作罢摆到两边去装装样子;做这些时仍然哼唱起自己编的曲调,听着像某种静谧的民谣。希格回到柜台里坐下托着腮,手指无意识地磨蹭脸上的鳞片:得到的断论是伊芙一点也不像莫伊拉。
窄的,狭长的列车啊
栽种下寂寞的鲁冰花
伊芙反反复复唱着几句旋律,没有歌词,只轻轻地飘出声来;像唱一个不会结束的季节、一次幽深的雨夜、一条闭环的小巷,没有灯、只有墙,将希格一声声困住。只有伊芙本人听不出,毛绒绒的尾巴依旧上下乱晃。重复到第六遍时希格跟上了她用手指在托盘上打的拍子,把方才想到的歌词唱出声。
车窗外原野有多刺眼
这样地让我想起她
敲盘子的叩叩声倏地停下,伊芙看向希格竖起尾巴,你会写歌词吗?
也不算擅长——不过能写而已。
希格边想伊芙和莫伊拉一点也不一样,边翻开手札低垂下眼去记歌词;不抬头,像赶路,一条荒草丛生的春天的路。伊芙并不能完全看懂希格的歌词,便懒得再纠结;受了冷遇也只管接着唱,想到哪句是哪句,一直到不知怎地绕回了开头段的曲调。
今年,雪和钟声会一起落下
我会等你回家
伊芙又开始不厌其烦地无意识哼着这么几个音,希格不再写新的歌词,一遍遍在心中跟她一起默默地唱;蘸水笔停留在纸上,透过三两页纸渗出小小的墨水点。她想加雷马也有一个永远寒冷的冬天,但每每提到雪时希格比冬天还要顽固地忘不了西部高地和云雾街。她又问一场雪的时间很长,一年的日子更是谈不上短,可是哪一个降神节开始她才能够让自己和那个猫魅族坐在同一只陆行鸟的背上,从空中再看一次雪?
希格抬起笔尖时意识到墨水已经透过了这页笔记的纸背,也意识到自己想起莫伊拉时,这个简短的名字总是像情书像诀别信,艰涩得让她开不了口。一次次跑进迷宫前她听惯了同伴的加油鼓劲,说惯了出发却不太说再见,直至连风险也司空见惯。在战场上闯荡久了的希格不擅长告别,就像一门心思前进的她不擅长说喜欢。
收起笔的动作让她无意中摆出了收起剑的姿势。但此时她的腰间没有地方再用来佩剑,她是烘焙师,不是冒险者。希格喝下最后一口卡米尔为她端来的花茶,——她看到杯底里下起迟来的大雪,来自某一夜灯光暗沉的忘忧骑士亭;那天她的背包没有系上拉链,魔导典的书脊从敞开的包里露出来,伊修加德的风声在回忆中模糊地呢喃,可是我没有剑。
“希格,可是我没有剑。”
她恍然发觉莫伊拉说得没错。莫伊拉没有剑,也没有魔导典;不能跟着她去东方,只有背过身拍一段神意之地断裂的墙,或是冲动之下跑到机工房端起一杆火枪。一颗子弹能飞的距离太短,再久也不过一次火花闪过的时间;但莫伊拉在属于那个火花的片刻里以她自己的步伐竭力奔跑,在她无暇顾及的地方拼命与她靠近。
“看见没有,我也拿得住枪了。”
伊芙的歌声骤然变作耳鸣,希格刚写下的歌词在她眼中成为交叠错乱的虚影。
原来她的刺剑即使不必反复擦拭都一直锋利,滞钝的只是她那被无数次刀光缭乱了的愧意与思念。
窄的,狭长的列车啊,栽种着寂寞的鲁冰花。希格跟着伊芙的拍子慢慢地弹,低低地唱,看打扮并不像拿过剑的冒险者;如果有顾客问起,她只回答自己曾在遥远的库尔札斯长大,因为难耐气候严寒才辗转到格里达尼亚,鲁冰花能让她感受到一丝故乡的记忆。
其实她确是曾在库尔札斯见过一回鲁冰花,在刚从乌尔达哈逃亡出来时路过的一户人家院子里。那时伊修加德的人还不太认得她,她便问房主那簇花朵的名字。裹在棉衣里的男主人上了年纪,和气地告诉她那是鲁冰花,他认识的为数不多耐寒又美丽的植物之一,种在院落里也算伊修加德难得的景致。分明是这么漂亮的花,名字的意思却是狼;不过也巧,他年轻时在库尔札斯做过猎手,接到过的委托好几次都是讨伐狼群。说着还硬要塞给她一小包花种,她忙解释自己是居无定所的旅行者,实在没办法带着一盆花四处游历,才推辞掉房子主人的好意。
在手札上记下这句歌词时,她仍是与那会儿一样居无定所,当然也没有在院子里种下大片的鲁冰花;但她突兀地记起鲁冰花的颜色,想到它其实很像莫伊拉的发色。只是莫伊拉并不像鲁冰花——她不是一匹狼,即使在端起枪时也不曾有属于狼的凶戾与野心;她自己一个人就是一场漫不停歇的雪。
莫伊拉,
希望你没遭遇过前些日子人们传说的、关于末日的那些事情,也希望最好你连听都没有听过。不过我记得你本就不太爱去偷听别人的话茬,虽然餐厅或者酒馆里的人讲话往往还蛮有意思;可惜你没这个习惯,莫伊拉——只是如果他们谈话时你曾竖起耳朵,大概也会听说有一支小小的乐队出现在黑衣森林角落里的酒馆。
近些日子我在这里打工,不作为退役的英雄和冒险者,只是烘焙或者弹弹琴;晚上就回到栖木旅馆去。如果你也恰好在附近旅行,我或许能在这里遇到你;也想你能碰巧地回到石屋,想你能见到我的来信。
伊芙说是所谓乐队,实则也仅仅在弹着伊芙写的谱子唱希格填的词,没什么严格的排练也没有正式的演出。客人少时便各练各的琴,客人稍多一点就在咖啡煮熟甜点烤好后一同弹上一遍。歌谣的节奏松松散散,实际上听起来,比起在招揽更像在催眠;希格不敢评价效果如何,但也是托伊芙的福,自己也是将她为了忙着冒险而丢下好久的键盘捡了起来。
今年,雪和钟声会一起落下,我会等你回家。每当伊芙唱到这句时,提米奥的吉他渐慢,卡米尔的提琴低沉,希格会抬眼看过在座的每个顾客,和声随着琴音久久盘旋。不觉间在店里唱歌已经从无所谓的活动成了每天例行的工作,但还没过多久伊芙就突然要请一段时间的假;理由同样无厘头,因为她刚攒下一点钱,想去太阳海岸的红莲节度假。于是演出自然而然地即将宣告尾声,等到伊芙动身的前两日就暂停,直到伊芙回来为止。
希格一面唱,一面想,她向来都没有家。被称作家的地方在黄昏湾、巨龙首营地、在丧灵钟直到宣布解散,也就只剩下了库尔札斯野外那座小小的石屋。
但她不是生在雪原的人,莫伊拉也不是;她们不会永远住在石屋中也不可能永远被困在那场大雪里。如果真的能在面前的几张桌子之间找到熟悉的暗红色眼睛,她该如何再以一名烘焙师的身份对莫伊拉说,若是我辞掉这份工作的话,要不要重新开始一起旅行,去库尔札斯以外的更多更遥远的地方摄影,哪怕我们今后依然没有家?
莫伊拉、莫伊拉。只有你是为了看到风景而旅行,只有你会因为我是我自己而与我在一起;你是唯一一个。
今年,雪和钟声会一起落下。
希格最后一次站在键盘后慢慢、慢慢地抬起头。
于是她的琴声掉进迎面撞上的相机镜头,右手被抽去所有力气,不轻不重地坠落在键盘上。
莫伊拉——
她跑得到可知宇宙的尽头,但她逃不过这个只属于她的黑洞。
——我会等你回家。
咖啡馆门外的溪流发出轻轻的脆响,每一寸水面的起伏映照出一朵细小的月光。拱桥旁希格与莫伊拉不去看彼此的眼睛,两人对峙一如那个夜里忘忧骑士亭地下的吧台;莫伊拉背靠栏杆面朝月色,希格伏在栏杆上望水中的波光。
莫伊拉。
终于是希格的思念先使沉默彻底崩溃决堤。她从栏杆上支撑起身体,向左侧挪了一小步,将头深深埋进了莫伊拉的肩膀。
我回来了。
希格的低喃微弱得像一句呓语。
面对希格时莫伊拉所有的情感都滞塞在喉咙里变成不知所措。她用一杆枪里火药弹射的速度逃离过,可弹道兜兜转转总是回到西部高地里某一片雪花的轨迹,轻而易举将她的欲盖弥彰一击贯穿。而今她面前的人是穿着流行外套的键盘乐手,没佩着刺剑或是带着魔导典,不会有人认出那是奔波前线的英雄阁下;然而只有她能够三番五次找到这对湛蓝的眼睛。——英雄、乐手、冒险者或是烘焙师都不重要,此时希格只是希格。
她只好侧过身子去将希格揽进怀中。分明追不上英雄的人是莫伊拉,被击溃的却是只身迎过末日的希格。
——希格,我想你了。
莫伊拉的信终于有了开头。
那句“逮捕我或者带走我吧”背后,她隐晦而简单的话语也终于第一次被说出口;端起火枪与你一起上路也好,成为火花甚至一项亟待你解决的委托也罢,弯子绕来绕去都不外乎希格,我想你了。想自己能追到她身边,枪口对准她正竭力搏杀的敌手,抑或骗她朝着飘雪的库尔札斯回一次头,得来一场英雄与狩猎对象短暂的重逢。
——希格,如果你这阵子去过忘忧骑士亭,可能会听店员说我临走之前多付了一杯酒钱。那个新来的店员算账从来都很清楚,我猜这份钱他不会白收,兴许能请你也喝上一杯。离开伊修加德后我去了黑衣森林的一家花店借宿,如果这回你闲下来的时间能长一点,我就回去收拾东西离开。
——毕竟你说过要带我去多玛。其实那封信寄来时我还在乌尔达哈,因为我知道你的旅途最初从那里出发。那现在呢?现在我还和从前一样喜欢甜食,可以领我尝尝你说的团子是什么口味吗?
——还有草原对吗?我去商店里查过地图。那时候你应该还在东方一带,对我说起的大概是叫做太阳神草原;草原上有你的同胞,我不是敖龙族,但我只是想被你带回一个叫故乡的地方,就像我陪着你一起回一次家。红玉海的海底呢?你说可惜我不会潜水,但如果不太难总归可以试试看。
她的声音比月色更轻比飞雪更沉,一字一句烫过希格的听觉,将她记忆里所有的信件点燃成火灾,钝钝地痛。
好,莫伊拉。我们一起。
希格摸到莫伊拉腰间防身的小手枪。枪没走火,但希格感到子弹钻进她的身体,让一切压抑和隐瞒破碎成尘埃。
我们去黄金港买三彩团子,去看奥萨德东岸的山峦、瀑布与蜿蜒的无二江,一直到红玉海去听听火山中的传说;或是去拍摄无边无际的草场,还有集市、衣楼、湖泊与峡谷。如果你喜欢,我们一同想办法去萨雷安岛的地下,那儿有比黑衣森林还神秘的林区与洞穴;再去近东一带最多彩的岛屿与城邦。
说到岛屿,要是你愿意——我们到谢尔达莱群岛去,让一座无名岛上的风景充实你的相机。
希格还想再说些什么,身上的通讯珠兀然响起。
——又要开始忙了吧,希格?
“冒险者,最近还好吗?巴尔德西昂分馆这里有从黑衣森林寄来给你的邮件。已经寄来了半个月还没有被取走,需要给你转送到新的地址吗?”
她可以逃到莫伊拉一生无法踏足的地方,但莫伊拉永远是她的天罗地网。
希格对莫伊拉无声地摇头。忽然想要借着月色说些什么,告白或眼泪,只是一切言语都被扼住在喉口。
面对她不再抵抗的一张情网。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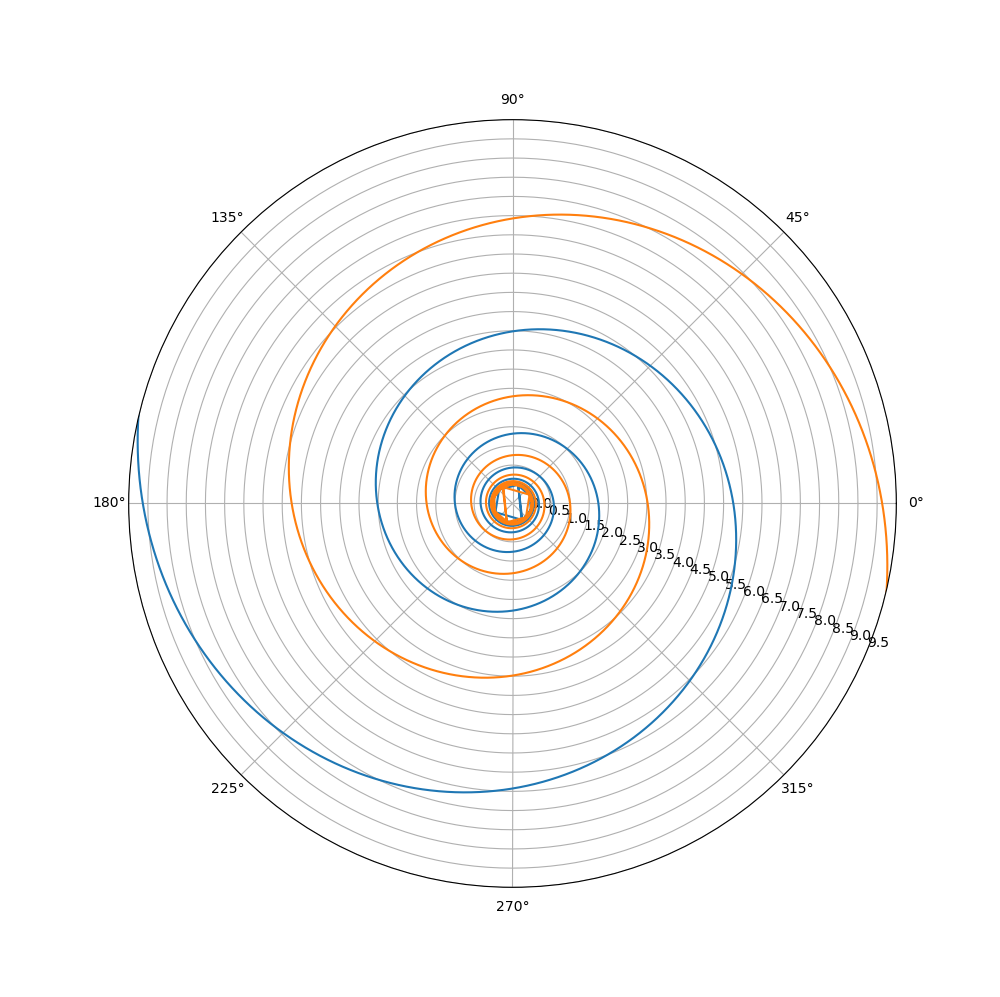
Comments |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