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库尔札斯向东南去的那段路她没觉得太长,想来是因为离开前最后一次检查背包,她把那杆又长又沉重的火枪拎出来丢在床底,换了把不起眼的小手枪揣到腰间。
莫伊拉的行李一如既往地只有一个背包,装着相机、粮食、钱和必要的药。太重的行囊像太长的头发,拾掇不清,又割舍不掉;于是那一天临走前她去忘忧骑士亭喝酒,好多杯下去兴致上来,管老板要来把剪刀,两剪子下去把长发砍到了齐肩。新来的服务生吓了一跳想去拦她,老板熟悉莫伊拉的性子,揪着衣领把店员拖回柜台去:别惹她,这家伙子弹打人可准呢。
她抱着背包在柜台睡到酒醒,多付了一杯酒的钱再上楼离开。
“不用找啦,得过一阵子再回来!”那天她顶着雪推开门回头大喊,声音有一半被吞进风中。
一路上行李轻便,她走走停停,一点点看风雪停下,树木泛绿,也哼起有些走调的童谣来。只是不幸她到底又迷了路,拿着地图弯弯绕绕几天,好不容易才找到森林里一幢木屋。远远望过去,是花丛簇拥着约有两层高的屋子;跑近了看,竖起的小黑板上写着是家旅馆。
她一头撞进门去,险些也撞上端着一盆古典玫瑰的苏里。
“咿——欢迎、光临!”苏里高高举起花盆,才没让莫伊拉的脑袋扎进初绽的玫瑰花中间。莫伊拉耳朵耷拉下去,闷闷地说声对不起,抓着捆在腰间的外套胡乱擦了擦眼镜,往门边挪挪给差点撞到的女人让路。
“没事没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买花,喝茶,还是说要住店?我叫苏里——苏里·嘉德纳。一般人可不会路过这家店,你是冒险者还是旅行家?”苏里的声音脆生生,快活又透亮。她将花盆摆回吧台,在围裙上拍拍沾到的土,倚着柜子回过身来。
一连串发问让莫伊拉张口结舌,没醉酒的时候她一向不爱说话;作为枪手的莫伊拉本来就不大需要讲话,除非是向雇主要钱,或者去酒馆花钱。她重新戴上眼镜,不安地甩一甩尾巴。“呃,住店……也不算冒险者,最近在旅行……”
“好的,好的,旅行家小姐!”苏里挥手一指柜台里挂着的另一块黑板,扭头又去搬那盆花,“价钱在这边,然后请在吧台上的那个笔记本登记一下名字;看你的样子,如果手头没钱也可以之后再付。你住多久?时间长一点的话兴许还可以免几天的费用——”
莫伊拉微弱地叹息一声,尾巴和脑袋也都重新垂下去;天知道她有多不擅长应付这类热情四溢的家伙。
在云雾街时,她结交的都是一帮拿命去交易钱的人,雇主和枪手之间只谈钱,只有在忘忧骑士亭混得久了的枪手与枪手,才能在醉后吐真言。酒馆写作Forgotten Knight,也读作Forgotten Night;酒醒以后,昨夜的一切就都翻了篇,他们还是沉默少言各自卖命的枪手。
她是个天生的杀手,她的第二位雇主说。莫伊拉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这话,她优柔寡断以至于不舍得离开库尔札斯,甚至来到机工房也是出于自暴自弃的赌气;但端起枪的手却稳得可怕,犯案更是明目张胆,总是结果了目标就消失在三更夜色里。
做久了,死相也看得久了。他们请她喝色泽艳丽的鸡尾酒,像称呼英雄一样叫她火花。可莫伊拉不明白。她感到自己也如一个摇摇欲坠的高脚杯,斟满了五颜六色,却还是空虚得能一眼望穿;她不要这样的英雄。
她也不想要希格是这样的英雄。
上一次告别希格后她没有为希格留新的地址,信还是一如既往寄到西部高地的石屋。——莫伊拉觉得希格写的字甚至比说的话要多。她们都不擅长讲话,希格留给莫伊拉的话语不及刺剑划过空气的声音尖锐,莫伊拉能回应的也只有酒馆里那句没头没尾的“可是我没有剑”。那些更细腻更柔软的心事被希格揉碎了写在信里,断断续续地寄给莫伊拉;莫伊拉偶尔回到石屋时,再断断续续地读。
莫伊拉很少回信,除非一时兴起地认真。她的字也认真,工整有力,一笔一划在信纸的背面都刻下印迹,墨水总是在第一个字母的起笔处洇开。——苏里的笔记本上,莫伊拉的名字前边也就这样多了个不大不小的黑墨水点。
苏里将古典玫瑰安置门外的花架上便折回来,探头看了看莫伊拉的签名。莫伊拉才想起来回应:“我会住…至少一个月,会不会更久不太好说。呃,手上有一点钱,可以先付一部分;其余的可以等我找到兼职以后中途再付…吧?”
“没问题,房间在楼上!”苏里三两下解开围裙丢到一边,推着莫伊拉的肩膀就上了楼。两层的木屋并不大,看上去并不比她在海雾村的小屋好多少;楼梯并排放下两个人都稍显拥挤,楼上大约也只隔出了两个房间。苏里推开楼梯右手边的房门——房门上还挂着一串干花。
“这里可以吗?”苏里先莫伊拉一步走进门去,推开书桌上方的窗子。“洗手间和浴室在走廊那一头;如果你喜欢,在楼下的餐桌和我一起吃饭就可以,或者下午一起喝点茶。要是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可以考虑替我把花送进城里,不过路有一点远!”
要适应这个人的性格,看来是这段旅行里一个蛮艰巨的任务。莫伊拉向苏里频频点头答应时心中暗道。
莫伊拉喜欢一觉睡到上午,再蹭蹭枕头、回顾一下刚刚做的梦,就到了一个不知该不该吃早饭的、尴尬的时间。
苏里在房间中装的窗帘不厚,隔着帘子还能够隐约看见窗外天空的颜色。许是因为阳光穿过窗帘偏偏打在莫伊拉脸上,这几天她醒得比平时还要早些。
一如既往地挣扎数分钟后,她克服困意爬起来,将乱成团的被子草草铺好,再推开窗;苏里为莫伊拉安排的房间刚好朝向太阳。但她前一阵子才习惯了在没有窗的地下室醒来,睁开眼还是昏暗的石墙。在云雾街时她不声不响地攒下来不少钱,一小部分花在酒馆,一小部分租用了地下室;剩下的存好,毕竟她一向没有稳定的工作。在拉诺西亚时她到一家小小的餐厅打工,后来才听说利姆萨·罗敏萨的另外一家店,那里的烤鱼在城中小有名气。
曾经打工的那家餐厅和苏里的花店有点像:店面不大,一家人开起了店,也就将那里当作自己的家。苏里住在二层楼梯的左手边,莫伊拉将房门推开一条缝向外张望,见她的房间大敞着门,楼下的厨房隐约传来水流声,应该是早已经开始工作。
莫伊拉将背包拎到桌上,翻出陪伴她许久的相机,腰包里揣着两块面包下了楼。临出门前苏里向她打招呼,她勉强应付两句,就跑进阳光里去;边翻找地图,还边拧过半个身子去向苏里挥挥手。无意间瞥见门口竖起的黑板,粉笔字已经从“旅店”改成了“客满”。她抓抓头发,这儿算上苏里的卧室也分明只有两间房,只容接待一两位客人,外边的招牌还硬要写着是旅店。
她的长发是在伊修加德最后一次微醺时剪短的,她还有印象。未曾精心修整过的发型显得生硬,摸起来的手感无端让她想起烈酒滑过喉咙,或是雪夜里永远冻得冰冷的扳机。
莫伊拉最后一次将镜头对准神意之地时就早预料到,城墙上锁孔般的缺口会困住她,从此她的每一步旅途都下雪。
于是她短暂地去过萨纳兰后,确实也在库尔札斯停留了许久;她不想辨别留住她的是那个积雪的邮箱,还是别的什么。于是她回到伊修加德,接过枪,直到那场比一封信还短得多的重逢。于是尽管她拍下过无数时分的库尔札斯,但仍记得那一张从遥遥的峭壁上拍下的双子湖。
花店向东走不远就是镜池,上午她半个身子探出窗户往外看,并不那么相似的两片水域慢慢重叠进印象中的那张照片里。
那是莫伊拉遇见希格前按下的最后一次快门。
莫伊拉背向镜池,踏着短靴,朝西北边走去。穿过陆行鸟叫声迭起的牧场,被拴住的陆行鸟朝她扑棱着双翼。她的目光穿过一片一片栅栏,最终只让相机对焦在围栏背后漆黑湿润的眼睛,可是没寻找到任何一只白色的陆行鸟。
她合起双眼,从前她们骑在鸟背上穿过库尔札斯的风,轻飘飘如偶尔脱落的白色羽毛。
再向前,她远远地望见巨树残存的根系。一端伸展向更高处,一端深埋在厚重的土壤里。
莫伊拉走近时,眼里映出巨木,也折射出巨龙的骸骨。她想起希格讲给她的传说,也想起希格的沉默。希格不太在她面前流泪,但她见过希格哭红的眼;她也不太开口问,她知道希格的旅途里有太多太多人擦肩而过,她只是转动在一个夜晚里,偶然离英雄最近的一颗行星。
莫伊拉想,自己可能从来不算一个例外;于是她很少说爱。唯一一次叫希格亲爱的,也模模糊糊地醉着。希格的信她翻来覆去地读过,至于她避而不谈的那些话语,希格也写得晦涩。所有故事和地母神忘迹的根系一样,和曾经存在于英雄身边的许多身影一样被久久掩埋。莫伊拉沿着巨树向上望,这个下午没有风,地底尽头望不见的星海也沉默。她不知道有没有传闻中的元素在周遭低语。
她只是忽然记起,刚刚经过牧场时似乎也经过值班的邮差。
她只是忽然地想要写一封信。
莫伊拉睁开双眼,这一次她没对上每天如约而至的日光。
天色微微明。噼啪的雨声叩在玻璃上,偶尔听得见树叶的摇摆私语。在库尔札斯与萨纳兰游历几个月的莫伊拉已经许久没见到过雨,遇上黑衣森林的雨天也还是头一遭。索性不吃早饭,也不拉开窗帘,坐在桌旁翻出了纸笔。
她与大多数人一样地讨厌雨天,但出门时又偏偏讨厌撑伞。曾经在海雾村独居的那几年,有一回也是个雨夜,她发现自己弄丢了一盒胶卷。她套上一件雨披,提起相机就冲下楼梯,冲出中桅塔,冲进蒙蒙的雨水里去——那天她一路跑到了海滩,将雨披搭在相机上,生生拍完了里边剩下的所有胶卷。回去后她发了场高烧,昏睡一天多,也勉强挺了过来。
或许你那里还没有;但黑衣森林今天下了雨,我在雨水对面为你写信。
莫伊拉的信件喜欢这样的开场白。没有称呼,没有亲爱的或者英雄阁下,仿佛这样就可以绕开她对感情所下的定义。但纵是她拥有多么干净工整的笔迹,写下的第一行还是不可避免地颤抖。她绕不开地问自己,这样也算作爱是吗?
她从雨水开始写起。
当你听我说起淋雨高烧的那一夜时,我们还躺在石屋的床上。我们喜欢在半夜攥住对方的手指,然后通宵或一夜无眠。那时你说我想一出是一出,会因为找不到胶卷而去大雨里拍空所有照片。你说我不像猫魅族,更像一只幼狼;骨头里盘踞着富有诱惑力的疯子的血脉。别太高看我;我其实做不到,否则我也是你口中的英雄。
他们叫你英雄,叫我火花。你去探求星球的呼唤,我在云雾街久久地盘旋,你知道我在等什么。
写下最后半句时莫伊拉握笔的右手显而易见地比平常更用力,几乎每个笔画的转角,字迹都要在稿纸上狠狠顿一下。
后来我想自己等不起,就揣着相机来了黑衣森林,暂住在弯枝牧场以南的一家花店,出门几步就是湖水;我看到的镜池很像那个冬天库尔札斯的双子池,地母神忘迹像连接命运的古老箴言。或许你疲于奔命的半路上会回头认真看看它们。——你说黑衣森林是你旅行之初探访的地方之一,可你还会回来吗?
你回不来。因为你真的像自己在九霄云舍里说的,去了东方以东的远方。
历经漫漫长路,今来之人与古往之人邂逅
为拯救世界,其寄希望于内心,迈向天宇之尽头
来到现在驻扎的旅店之前,我还听着过路的吟游诗人唱着英雄的歌。你去了比天穹还高远的地方,也许那里收不到信件、调不出冻雾鸡尾酒、建不起一栋石屋。你不可能永远住在那座石屋里,因为你本来就漂泊。我从来也漂泊,我们是两只陆行鸟曾从同一个驿站边擦肩而过。
希格,我的英雄,你听我说。
莫伊拉在信纸的末尾停留了好久好久。她想,如果天黑之前雨停了,她就将最后一段话写下来。
其实我们钟情的彼此都活在旅途的某一个片刻里。
除非现在,你也愿意重新去爱一个陌生人。
黑衣森林的摄影师
依然是一段不清不楚的情话。
将中央林区差不多拍了个遍以后,莫伊拉开始思量着帮苏里打打零工。背包里的钱还够用,但她不想动用这笔存款。她知道旅行中总有个万一,需要随时防备着意外。
苏里答应得很爽快,交代了客户的地址和交货的时间。顾客将时间约在第二日的下午,格里达尼亚新街的魔女咖啡馆。
苏里提起水壶,熟稔地浇灌架子上上的一盆盆鲜花。水珠顺着花叶向下滚动,而后便和另一颗水珠汇聚;叶片微不可察地颤动,水滴倒映出的五彩渐渐缩小,坍塌在午后的天气里。有一簇花略略显得衰败,她将它端到最高处,一盆温暖的金黄就迎上了太阳。
“今天有什么事吗?”她问莫伊拉。
“还没安排。是有事需要我帮忙吗?”莫伊拉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倚在门边看苏里干活;这么多天下来她多少也习惯了苏里的热情。
花架上的盆栽植物被打理完毕,苏里将水壶放回门口的围栏边,笑起来眉眼弯弯,让莫伊拉难以拒绝:“帮忙倒是没有,——不过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喝下午茶?”
莫伊拉才记起刚住进来时,苏里好像对自己说过类似的话。
黄色格纹的布料铺在木桌上,苏里将泡好的花果茶倒进玻璃杯。莫伊拉摸了摸杯壁,将手缩回去:她怕烫。
苏里没太在意,自顾自吹了吹杯中的茶水:“聊聊你吧。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平时都出去做点什么?你的家在哪?以前在哪里旅行,又干些什么活?”
又是一连串的提问。莫伊拉低下头,杯中淡红色的茶水里,有她暗红色眼睛的影子。
她从自己的家讲起——如果一定要说家的话,我想应该是海雾村。莫伊拉讲得很慢,毕竟茶不是酒,她要从记忆里一点点拣出细碎的语言,再串起一个故事来。
我想应该是海雾村,我出生在那里,只是父母不太管我。他们是一对再平庸不过的渔民,一个是三天两头出海的渔夫,一个就戴着头巾在港口卖鱼,顺便等着丈夫回来;直到某一年的海啸把他们连带着他们的生鱼片和烤鱼干卷走。
“海啸——”苏里一口一口抿着茶,“我还没去过拉诺西亚,但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啊,是说第七灵灾的那一次。”
我看到那场海啸的照片也是在报纸上。那时候我也不算小孩子了,但还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我暂时卖了从前住的房子,搬进中桅塔的公寓去,也算有了一笔能够用来生活的钱。
后来像你现在看到的一样,我四处打工,腻了就去旅行,在拉诺西亚、萨纳兰和库尔札斯,黑衣森林还是第一次来。我给利姆萨·罗敏萨和乌尔达哈的小报社当过记者,也在海雾村的摄影棚里干过活,后来在餐厅里端过盘子,也在伊修加德那边…嗯,偶尔在伊修加德接过一点委托。
“多好呀。”苏里为自己又倒满一杯,热气重新从杯口氤氲出来。
很好吗?
“灵灾之前我可是被父母要求守着这家花店的,然后第七灵灾过去,花店里就剩下了我。所以我走不出去,我要守在这片森林里。多好呀,莫伊拉小姐,你是一个自由的旅行家。”她的声音轻飘飘,呵出来,就消散在餐厅温热的花果香里。
莫伊拉的茶水放凉了,她一口气喝下一半。——在这儿住了那么久,苏里,你有过恋人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苏里的声音中又含着笑意了,“实话说曾经有过,是格里达尼亚一个年轻的制革匠。那会儿他路过这家店,然后一住就是两个星期。临走前他说他总有一天要辞掉工作,和我一起经营这家花店;只不过有一天我寄到格里达尼亚的信再也没有回音。”
后来呢?
“后来我去格里达尼亚送货的一个下午,真的去他留下的地址找过他。也是个大晴天,我穿的是平时不怎么会拿出来的一件礼裙;在衣柜里叠了很久,穿到身上还能看出皱褶。那儿的人们告诉我,他确实辞掉了工作,但没有人听说他去了哪里。那天以后我就没再跑去问过,但我猜他不会再回来。”
“你呢,也有过恋人吗?”
莫伊拉不急着回答。她喝掉剩下半杯茶,抬起眼看桌对面的苏里;灯光下苏里的短发垂到了肩头。而她的笑还停滞在嘴角,静静的像房子外那盆凋败一半的花。
我呢。莫伊拉的目光越过苏里的肩膀,一路探到窗外明朗的夏天里去。
你看,我在每一个地方都待不久,在这家花店里也一样。这里是旅行者偶尔停下的旅馆,只有你将它当作家。
所以呀,我们的身边都找不到一个人,陪着我们慢慢变化。
即将送到格里达尼亚的货物是一捧精致的花束。莫伊拉坐在桌旁托着腮看苏里包装,几棵魔女草,夹几株细小的紫灯花;裹两层包装纸,用丝带捆扎。
莫伊拉照旧将相机与地图塞进腰包,而后向北出发。短靴踏过沙土,走过树林荫蔽的小径,绕过耸起的小丘与潺潺的水域,来到这座属于森林的城市。魔女咖啡馆并不难找,入城沿路径直走,左手边便是。她如约将花束交给店长,本想再要一杯咖啡,但想到格里达尼亚的咖啡可能几乎不加牛奶,只好悻悻作罢,点了花草茶在店铺的角落坐下。
分明是家咖啡馆,可她没嗅到咖啡浓醇的香气;这里的气息和流沙屋大同小异。莫伊拉想起一个金发蓝眼的影子,她回到库尔札斯后她们就没有再见过面。她们是一起喝过一杯酒的关系,也仅止于此;卡洛塔是四处兼职、偶然在红玉大路替班的舞女,莫伊拉是四海为家、为了寻找另一个人而路过乌尔达哈的旅者。
为了寻找另一个人,为了来到一名英雄旅途开始的地方,仿佛拼命搜刮来自过去的一点点碎片,她就能拼凑出一条通道,然后钻进那个人的回忆里。可关于希格的故事莫伊拉独独不敢说出口,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找什么也不愿意说爱,尽管她心知肚明。
年轻的侍者端来了她的花草茶,用衣袖抹一把额头的汗水,又一溜小跑去应付下一位顾客。茶里加了冰,莫伊拉用小小的匙子去搅,冰块就叮当地磕在半透明的杯子上,像那个过路诗人叮当地调着琴音。
咖啡馆里也时而传来碰杯声。莫伊拉循声一桌一桌看过去,多半是冒险者模样,墙边还斜靠着三四把被新兵擦得发亮的长枪。两个穿着礼裙的女人在她不远处的桌子攀谈,她听了两句,大约是埋怨咖啡馆里的冒险者越聚越多,人人都想成为光之战士,可身上没修炼出光之力,倒是沾了一身酒气。
“…下一次要不要去薰衣草苗圃的咖啡店?味道比起缪恩磨出来的差了点,但是至少安静,没有这群只会吹嘘自己的酒鬼。倒是有人从下午一直坐到晚上,为了等晚上演出的乐队。所以白天的人应该会比晚上少一些,——没记错的话,下周的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出。…听说是三位姑娘,还有位个头很高的小伙子。他们唱的歌没人听过,我猜是从什么小村子流传下来的民谣…”
花草茶里的冰块融化开一半,棱角被温度打磨圆润。莫伊拉咽下一小口,抿进一颗小小的冰,想起她在忘忧骑士亭点的鸡尾酒即使不加冰也永远那么冷。
忘忧骑士亭没来过诗人,也没来过乐队唱民歌。那是家纯粹的酒馆,一腔热血的骑士与以她为首的混混喝一样的酒,店员娴熟地在手指间翻转量酒器,记得哪位客人想要烈酒,哪位客人不加冰块,所有人的故事都在这里浸泡。她只听到过一回荒腔走板的歌声,来自一位酗酒的敖龙族女士;醉得厉害,打翻了酒壶,长袍都被甩落到地板上。她本想将女人脸颊上的红晕和眼里的迷蒙装进胶卷,摸向口袋却只碰到一把手枪。
那天临走前她捡起长袍,披回了女人肩上。
莫伊拉说不出为什么一定要去拍摄一支最后一次演唱民谣的乐队,就像她说不出自己为什么曾穿过一群难以对付的魔物去寻找独角兽。唯一的理由是她想,一切都因为她想;像跑到海雾村的海滩上淋雨、突然从乌尔达哈折回库尔札斯,对独自旅行的人而言,直觉就是地图唯一正确的方向。
她回到花店向苏里交了当天的差,向镜池栈桥的码头去。等到月光从湖水上泛起来,船头就悠悠地解开缆绳,让他们从月影的正中央划过。
等到莫伊拉跑进薰衣草苗圃的园区,才恍然意识到忘记了问清详细的地址。夜幕笼罩后四下无人,商店也打烊,她奔跑在错综的小径上,切口整齐的短发被风吹乱。路灯的亮度聊胜于无,还不及那些房屋的窗口溢出的暖黄色灯光。莫伊拉循着一扇扇窗找过去,想听清随着灯光一同流泻而出的,有没有一首听起来像是民谣的歌。
最终她停在了面朝小桥的一方院子里,房屋比苏里的花店还小了一圈,有着砖红色的屋顶;一张长椅放置在葡萄架下,上边还停留着几片不知哪里落下的花瓣,院落中大小不一的踏脚石延伸向歌声传来的地方。
营业中。门口悬挂的招牌写着。
莫伊拉慢慢推开门钻进去,即使已经尽量放轻动作,门轴仍不可避免地吱呀作响。其实店里的顾客并不多,两只手都数得过来;最靠近入口处的桌上有客人注意到她,便友好地招呼,“嘿。运气不错,听到了最后一首歌。”
一支民谣乐队的最后一首歌。莫伊拉低下头去摆弄相机,再抬起头时乐手已经被装在取景框里。
窄的,狭长的列车啊
栽种下寂寞的鲁冰花
车窗外原野有多刺眼
这样地让我想起她
扶着话筒的歌手有青碧色的眼瞳。深黑的长发别了几枚发卡,一半拢在背后,一半太短,散落在脸颊旁边。莫伊拉按下快门时,歌手的视线刚好对上她的镜头,于是胶卷里记录下一名猫魅族澄澈的眼眸。她也拥有着和眼眸同样澄净而轻柔的音色,如同娓娓讲述一个久远的秘密。
轨道载着几百几千个故事呢
几千座远远近近的城市
车窗外月光有多刺眼
这样地让我想起她
站在中央的一对精灵族穿着同样的衣装,银发的少女手上是提琴,金发的青年怀中是吉他。他们不开口,故事都写在提琴悠长悠长的吟唱里,吉他的节奏为叙述写下注脚。青年拨弦的手清瘦颀长,一声声拨进莫伊拉躲在相机后的双眼。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记起了什么:记得有一只手握住过刺剑,记得刺剑指向一条苏醒的龙。
窄的,狭长的列车啊
栽种下寂寞的鲁冰花
今年,雪和钟声会一起落下
我会等你回家
键盘背后的敖龙族边弹着琴边为歌手和声,歌谣唱到结尾的那一句,眼神便短暂地从琴键上离开,淡淡瞥向镜头。
莫伊拉本可以敏锐地听见琴声快了一拍。
但她的相机对焦在了一双蓝色的海域。
她听到提琴的尾音下沉再下沉,最终坠毁在那对眼睛里。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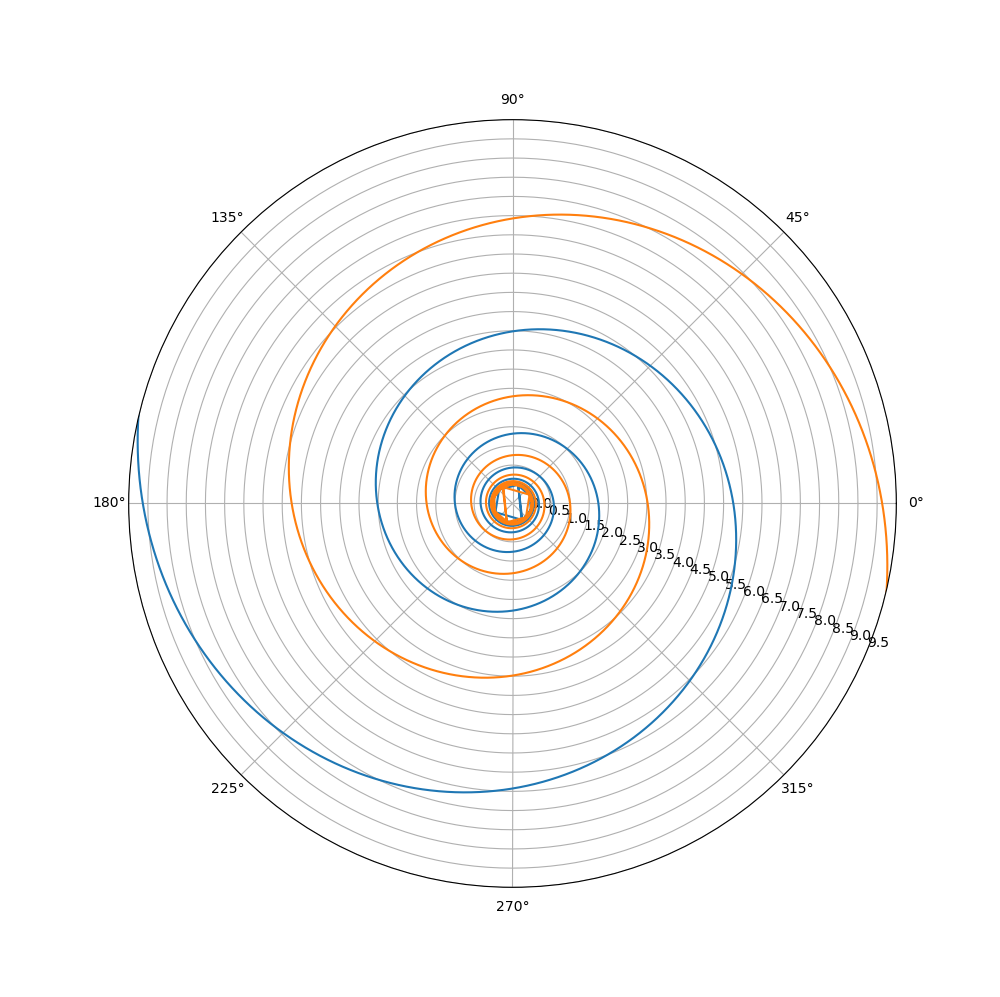
Comments | NOTHING